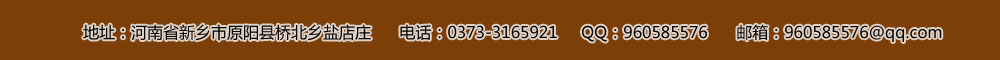清平乐背后的大宋王朝庆历新政到王
最近大热的《清平乐》已经正式收官,它以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笔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宋代生活画卷,让很多现代人也不禁对那个时代浮想联翩,甚至有些心驰神往。但正如《清明上河图》中暗含着多处危机,《清平乐》背后也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治理难题,或许直到今天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仍是围绕“做蛋糕”和“分蛋糕”展开的。
《清平乐》做蛋糕的人是谁呢?当然是老百姓,是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正如山海关外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说:“没有劳动人民,吃啥?没有劳动人民,穿啥?吃穿都没有,你还臭美啥!”
劳动人民辛苦劳作,自然是要分蛋糕的,这叫按劳分配。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暴力机关的垄断者,自然也要分走一些,这属于自然权利的让渡,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协调社会生产。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是有些片面的,改写历史需要两根柱子,而儒家只强调公共服务一项,要是碰到“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宣帝还好,如果遇到过于“仁柔”的汉元帝,那就要出问题。
我们一般把参与蛋糕分配的主体归纳为国与民两类,现在也有很多人这么看,比如网上常有“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之争。但仔细想一想,民就是老百姓,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组成的;国呢?国家是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将其实体化的是谁呢?是管理者,放到古代,就是官僚,当然,还有这一集团的后备军,豪强地主。
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是人就要讲究成本核算,老百姓肯定是想尽量少缴税而获取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古代官僚、豪强地主则想通过税收、特权多赚钱而少承担些公共服务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封建王朝总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税越收越多,治理能力越来越差,钱都去哪了呢?自然是进了官僚与豪强地主们的腰包,连皇帝内帑与国库公帑都未必有得赚,比如大明崇祯天子。
具体到宋王朝,我们总觉得那是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好时代,可再看看当事人的评价,比如朱熹,他是一代大儒,又是个当权派,却也直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同时代的蔡戡也认为:“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清代学者赵翼更加不留情面,他讲,宋代“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也就是说,你朱熹、蔡戡之流不要像“白左”一样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宋代这样收税是为了维护谁的利益啊?侬要晓得。
事实的确如此,有宋一代长达三百余年,变化颇多,但政治底色却始终未变,那就是三朝元老文彦博所明言的,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宋代统治基础是士大夫阶层,如此一来,搞出“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统治者总是要扩大其统治基础的,所以,在以关陇贵族、山东士族为统治基础的隋唐时期,尽管朝廷首创科举制度,却也未必有多重视,顶多是张官僚后备军入场券;宋则不然,宝贝得不得了,仁宗皇帝他爹真宗还御制《劝学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全文如下: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儒家教育与科举制度大规模扩招相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体系迅速扩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也就随之而来;与此同时,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也都有冗兵之弊,官员俸禄和兵饷支出日益成为朝廷无法承受的负担,是为“三冗”。这个问题在仁宗时代便已经十分突出,改革积弊便提上了日程,是为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范仲淹剧照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要做减法,思路也很简单,既然冗员太多、人浮于事,那就裁掉好了,大宋官家不养吃白饭的。富弼对此表示担忧,提醒范仲淹道:“十二丈(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耶!”不想老范根本不上道,霸气回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不过同样是哭,一家士大夫的嗓门显然远远大过一路百姓,不久之后,范仲淹被仁宗罢免,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新政迅速失败深深触动了一名初出茅庐的有志青年,使他在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放弃进京入馆阁的机会,主动申请调任鄞县知县。二十余年之后,当初的有志青年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与另一位锐意革新的青年皇帝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共同主导了一场史诗级大改革——王安石变法。
有了范仲淹因触动官僚集团存量而失败的前车之鉴,王安石与宋神宗这对君臣便打起了增量改革的主意,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加强朝廷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扩大税源,以期达到削弱官僚集团与提高治理能力的目的。
王荆公安石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王安石变法虽然打着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旗号,意图化官僚垄断为国家垄断,进而增强国力,不想却被从小砸缸的司马光同志一眼看穿,直指要害:“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你王安石想从我们官僚身上剜肉补疮,不怕老子扛着红旗反红旗吗?反正羊毛都出在羊身上,薅的机会总是有的,毕竟政策执行总要官僚集团来吧?所以说啊,小王同志还要提高一下姿势水平,官僚集团不怕任何政策变动,只怕根本没有政策,新旧党争之下,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事情果然不出司马光之所料,王安石变法政策出台后,遭到官僚集团集体反对,纷纷消极怠工。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只能加强三司使权力,在原有官僚机构外架设各种工作指导小组,拔擢“希图幸进”的吕惠卿等来实操,其结果就是虽然天量社会财富通过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之手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央政府以及皇室金库,使神宗朝财政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而在变法实行初期,青苗法和免役法也确实为中下层有产者带来了一定好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官僚集团借着改革东风,也狠狠发了笔政策财,至于钱从哪来这个问题,司马光已经说得很清楚,自然是百姓头上嘛!到徽宗时,官僚机构膨胀恶果愈发凸显,新法已经完全变质,还搞出了“方腊起义”,这也意味着王安石所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变法理念已彻底失败。
尽管南宋被迫丢掉了淮河以北的“财政包袱”,朝廷也直接定都于江南这个“财赋之地”,但“三冗”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央财政日趋窘迫。为缓解中央财政的紧张局面,“奸相”贾似道被迫推行“公田法”改革,再次触动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对于彼时的江南士大夫、大地主们来说,由已经开始汉化的蒙古人当皇帝,似乎比贾似道当宰相时的“公田法”要好,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于是,公元年,蒙古大军再次南下,江南士大夫一改襄阳抗战的顽强作风,望风而降,失去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南宋很快就灭亡了。
崖山海战至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宋王朝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很明显是士大夫们的嘛!是“在乎山水之间”的六一居士,是“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苏东坡好友张先,就说东坡先生,一个贬谪之人,物质待遇仍然不低,自然能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同样是面对下雨,方腊、杨幺怕是要骂娘的。当然,在士大夫们的笔下,宋王朝的历史形象是不会太差的,虽未必有文治武功,但至少还能“清平乐”,毕竟历史虽然无法更改,可其解释权还在笔杆子手里,“臣光曰”嘛!
最近更新